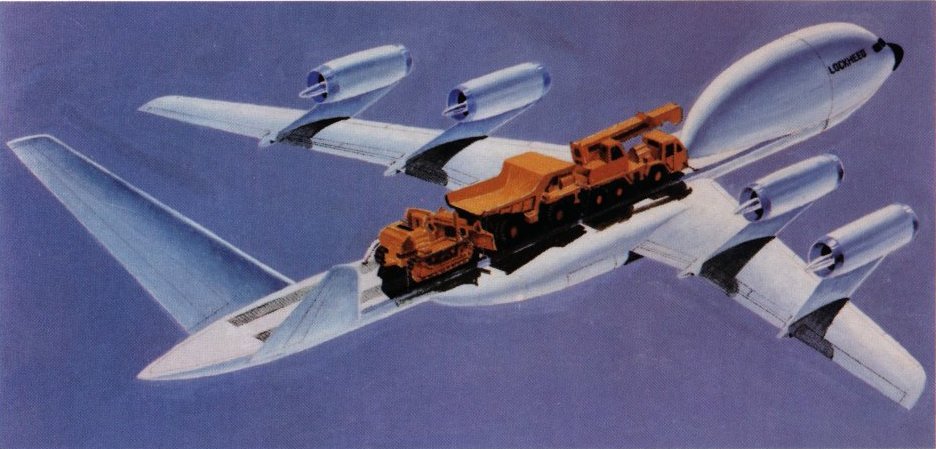[编者按]
她们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同时也是诗人。她们以柔软细腻的诗心,勾勒着生活点滴、倾诉着爱恨情仇。她们用人生来膜拜诗歌,也用诗歌温暖人生。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中国诗歌网最新推出“女诗人系列”访谈,带你近距离欣赏那一道道亮丽风景。欲知“女诗人养成记”,请随我们一起,探访她们的生活现场,感受她们文字中的温度。
[精彩回顾]
“走近女诗人”【第四期】 胡茗茗:诗歌、电影、瑜伽——“最有画面感”的女诗人
“走近女诗人”【第三期】 春树:叛逆的青春 游走中飞扬的诗意
“走近女诗人”【第二期】 李小洛:做一个安静而耐心的手艺人
“走近女诗人”【第一期】 颜梅玖:真正的诗人,手中永远握着一支不存在的笔
“走近女诗人”系列访谈 【第5期】

潇潇
潇潇(诗人主页),诗人、画家。“中国现代诗编年史丛书”主编、《大诗歌》《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特刊》执行主编。1993年主编了中国现代诗编年史丛书《前朦胧诗全集》《朦胧诗全集》《后朦胧诗全集》《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全集》。出版诗集有:《树下的女人与诗歌》《踮起脚尖的时间》《比忧伤更忧伤》等。作品被翻译成德、英、日、法、韩、越南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孟加拉语、罗马尼亚语等并在国外的报刊杂志发表。其绘画作品参加了“中国当代诗人艺术展”;“中国当代文人书画展”等。长诗《另一个世界的悲歌》被评为九十年代女性文学代表作之一。曾获首届“探索诗”奖、“中国第三代诗歌功德奖”、“汶川抗震救灾优秀志愿者奖”、“第二届中国诗剧场•诗歌奖”、“第一朗读者诗歌成就奖”、2013《现代青年》年度人物•最佳青年诗人、第五届“闻一多诗歌奖”、2015中国实力诗人奖、2016年罗马尼亚图多尔•阿尔盖齐传统国际文学奖等,并授予潇潇为罗马尼亚荣誉市民。
2016年5月22日,在特尔古卡尔布那斯特市,罗马尼亚作家协会主席、著名评论家NicolaeManolescu把图多尔•阿尔盖齐传统国际文学奖获奖证书颁发给潇潇,以鼓励她多年来诗歌的世界性创作,以及关注人类的压迫苦难的诗性表达。同时,该市市长给潇潇颁发了特尔古卡尔布那斯特市的荣誉市民证书。在纪念罗马尼亚伟大诗人图多尔•阿尔盖齐的博物馆里,挂上了潇潇的照片。与那些富有国际声望的作家一起,潇潇的照片将永久性地悬挂在博物馆的墙上。诗人潇潇获得罗马尼亚图多尔•阿尔盖齐传统国际文学奖。她是第一个获得此殊荣的亚洲人,此奖也是第一次颁发给外国女性。

在纪念罗马尼亚伟大诗人图多尔•阿尔盖齐的博物馆里,潇潇的照片将永久悬挂
深挚而热烈,朴素而饱满,似血似泪,亦哭亦歌。潇潇的诗以汹涌而澎湃的抒情力量和丰沛而鲜明的女性特质,传达了生活所赋予她的致命经验。这里有灵魂的审视与自剖,有爱情的悲歌与祭奠,有生命的坚忍与脆弱,有命运的承受与抗辩,给人以切肤的情感撞击与精神震撼。生活没有教会她幽曲的隐喻与华美的修辞,却赋予她一泄千里的狂歌与直抵内心的锐利。在历经漫长的修持与磨砺之后,这组《灵魂挽歌》标志着潇潇的诗歌写作令人欣悦的自我蜕变与升华。不止如此,她长期以来为当代诗歌事业所奉献的执着努力也值得尊敬。
——潇潇获第五届“闻一多诗歌奖”的授奖词
语言是她缓解巨痛的杜冷丁,她在词的根部发言,她以全部的热情与爱投入世界的怀抱,她惟一的目的是对诗的阐述。她是第三代诗歌之后仍然保持旺盛的创作激情的极少数女诗人,她的诗里调和了蜜糖与苦酒,她把诗喂给被爱遗弃的孩子,同时抚慰苦修的精神兄弟。她的诗是时代的证词,是个人隐秘的血,滚烫与冰冷,尖叫与沉默都是她诗歌的一部分。她手握思想的斧子向黑暗的身体下手,她寻找生命意义的勇气让她拥有探求世界的灵魂。她把岁月积累的个人生命经验,那些看起来并不宏大的事物与细节,经过语言捣碎与良心的一次次发酵,变成了她个人既私密又有强烈火药味道的“潇潇式词源”,越过一个时代的遮蔽,最后呈现出那个时代被集体几乎缄默的宏大主题和精神伤痛气息。鉴于此,现将2015中国桃花潭国际诗歌艺术节“中国实力诗人奖”授予潇潇女士。
——2015年潇潇获“中国实力诗人”的授奖辞
一
花语:很多年前的《诗歌报》上,大红标题的青春四少女就有您,那时您多大,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处女作还记得吗?

豆蔻年华的潇潇(摄于1982年左右)
潇潇:记得八十年代中期,《诗歌报》的头版头条,套红的大标题:“引人注目的四少女”,选登了全国四个省的女孩子的诗作。上面标着:四川潇潇,18岁。我大约从1983年开始写诗发表作品,到今天整整33年了,算一个老诗人吧!处女作在一次动荡的搬迁中遗失了,像我生活的一个隐喻,遗失的,最好不要轻易提起。
二
花语:听说您是成都人,从小生活在部队大院,而北漂后,您一直生活在北京,南北方地域的差异,是否对您造成某种困扰,成都和北京,您更喜欢哪里?

1988年在成都的一片桃花林
潇潇:严格说,我不算成都人。虽然我在成都生活了近十年,户口也在那里。我跟父母随军,从小在部队大院吃喝拉撒。随父亲的工作调动,我在乐山、犍为都生活过。现在,我更愿意说,自己是犍为人。那里存着我青少年时代的光阴。那是一个依偎在岷江边的小县城,每到夏天傍晚,几乎全城人都倾巢出动,到河边叉水乘凉,小买卖,喝茶,打牌,恋爱,谈天说地……河水在灯火中流淌,闪烁,发出低低的哗哗声,仿佛给岸边的人哼着清凉的小调。那景象,不摆了!馋死大都市被困在高楼大厦的人。过去,我逃避说起这个山水清秀的小县城,怕别人看不起一个从小地方来的女孩子,那时,我的自信像一粒绿豆那么小。

90年代在北京京郊留影
在北京生活25年了,我没有感觉到什么南北方差异困扰。从飘到北京开始,我就自然生根发芽。也许,我是那种落到哪块土里都能生根开花的,能不能结果不一定。哈哈。我喜欢北京的大醇小疵,此起彼伏的文化氛围。讨厌雾霾,堵车,讨厌大而无当的东奔西走的饭局。喜欢成都的吃喝,小腐朽,小温情。讨厌盆地意识的恶俗,虚荣,小心机,浅薄,谎话连篇。
三
花语:您最近刚刚获得2016罗马尼亚图多尔.阿尔盖齐诗歌奖,听说您是得到此奖的唯一亚洲诗人,为国争了光,得到此奖,有何感想?

罗马尼亚作家协会主席Nicolae Manolescu先生颁发给潇潇的图多尔•阿尔盖齐传统国际文学奖证书
潇潇:2016年5月22日,在特尔古卡尔布那斯特市,罗马尼亚作家协会主席、著名评论家Nicolae Manolescu把图多尔•阿尔盖齐传统国际文学奖获奖证书颁发给我,以鼓励我多年来诗歌的世界性创作,以及关注人类的压迫苦难的诗性表达。同时,该市市长给我颁发了特尔古卡尔布那斯特市的荣誉市民证书。在纪念罗马尼亚伟大诗人图多尔•阿尔盖齐的博物馆里,挂上了我的照片。与那些富有国际声望的作家一起,我的照片将永久性地悬挂在博物馆的墙上。我是第一个获得此殊荣的亚洲人,此奖也是第一次颁发给外国女性。

罗马尼亚作家协会主席、著名评论家Nicolae Manolescu先生给潇潇颁发图多尔•阿尔盖齐传统国际文学奖证书

2016年5月22日在图多尔•阿尔盖齐的博物馆潇潇与布加勒斯特作家协会主席、诗人、剧作家霍利亚•戈贝先生(左)和该文学奖的组织者(右)一起合影,背后墙上悬挂着潇潇的照片。
图多尔•阿尔盖齐传统国际文学奖已经颁发36届了,是以罗马尼亚的“民族诗人”,图多尔•阿尔盖齐的名字命名的。图多尔•阿尔盖齐(1880-1967)罗马尼亚著名诗人、散文家。作品深刻、生动地反映了时代的脉搏和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蹲过德国人的牢房。曾三次获罗马尼亚国家奖金。他被誉为罗马尼亚“诗歌之神,罗马尼亚诗歌苍穹上一颗光芒四射的星星”。著有诗集《和谐的词》、《人的赞歌》,散文集《木头圣像》等。世界著名的诗人马林•索雷斯库曾获得此奖。
坦率说,我获得此殊荣有些意外。感觉天上的馅饼不小心砸到我头上了。到罗马利亚之前,我一直不知道,还以为是受邀请去参加一个文学节呢!差一点还因为签证难办,放弃不去的念头。
四
花语:看过您最近一组诗作,感觉您的表达较之于早期作品,更犀利、更精准、更通透、更富哲理和禅意。作为一名书写多年的诗人,要保持旺盛的创造力并突破自身的瓶颈不易,您是怎么做到?
潇潇:坦率说,我还没有感觉到瓶颈的滋味。我的创作一直在路上,在成长,在语言、文字的炼金术中,我还是一个学徒。我只能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写下去,能走多远,看老天爷给我多少恩宠?
五
花语:听说您参加过2008汶川抗震救灾志愿者队,亲自深入过重灾区,为此还获得"汶川抗震救灾优秀志愿者奖",能否说说现场遇到的危险,和当时的感受?

潇潇与灾区的孩子们
潇潇:我是2008年5月17号报名去灾区当志愿者的。在受灾沿途,死亡无处不在,伸手可触,生命渺小而脆弱。常常遇见死亡在弯曲的盘山道上冒着青烟与我们捉迷藏。记得我刚到绵阳时,当晚就预报6.8-7级的余震。五月的这个夜晚,我人生中第一次睡在一个空旷的工厂水泥地上,暴雨通宵点击着薄薄的帐篷。余震的晃动,蚊虫叮咬后留下的瘙痒,终生难忘。
去平武送救灾物资的路上,山体滑坡,我们被困在废墟上,雨水与堰塞湖形成了新的小河流。河滩上,到处都撒着一团一团的白石灰,给浅埋在下面的尸体消毒。实在没有多余的人手,把遍地的死亡挖出来,重新深埋。这时,我读到了世界上最孤寂、最绝望的诗篇,那是蹲在废墟的河边,两个农民失去全家老小三代的眼神!而我的脚下正踩着他们被山体掩埋的家人和整个被掩埋的村庄。我把随身带着的食物和饮用水分给了他们,这路过的安慰像河床上那些消毒石灰,一样苍白,一样肤浅!我灵魂的余震绝不仅仅是8.0级的震动。面对在劫难逃的生命与死亡,我们往日斤斤计较的诗艺就像一具流干了血液的躯体,那么空洞!

行动!只有劳动才能在一次次高强度的疲惫中攥紧生命延续的滚烫感觉,听见血液流淌出的真实声音,让良心得到救赎。这就是2009年初我为什么要向四川省委宣传部打报告做“5.12汶川大地震周年祭”的内心动力,后来与他们一起策划了《铭记5·12:这里是四川,这里是中国》大型诗歌朗诵会。

搬运物资后,喝水时孙队长、队医大家与潇潇的合影
在灾区,人人在救援现场都自然呈现了善良、高贵的一面,我触摸到了在大灾难面前人性的光辉。从死亡的领土上,人类抢回了那一颗残缺而勇敢的心!每一个在这片死土上呼吸的生命都是亲人!这种感动在今天依然温暖着我。记得在灾区做志愿者的最后一个晚上,为了告别的纪念,我站在麦田的帐篷旁,给战友们朗诵了我的诗:《汶川——祖国的心与你一起跳动》。在这个时候,大多数与我并肩劳动,起早贪黑救灾抢险的志愿者们才知道我是诗人,他们一一与我拥抱,认真地把我的诗抄写在笔记本上。临行之前,他们诚恳地对我说:“潇潇,以前我们对诗人有很多误解,因为你,以后再也不说诗人的坏话了”。这让我非常震撼,也促使我对当下“自以为是的诗歌小圈子”进行反思。诗歌的经典不是象牙塔的金字招牌,也不是挂在空中楼阁的玄学,与无事生非的口水,而是种植在现实土壤里生根、发芽、开花,最后结出的灵魂之果,是从心灵流淌出来的温泉。如果你的诗歌有强大的精神坚守和坚实的艺术质地,你终究会被人们善待。诗歌在当下必须要有担当意识。
六
花语:您在几乎所有的志愿者队伍都撤出了距堰塞湖可能垮塌最近的桑枣镇的情况下,您又单独返回过那里,为什么?
潇潇:我得到消息:堰塞湖随时都有可能垮塌!我怕堰塞湖真正垮塌下来!如果我没赶回桑枣镇,告诉在那里的志愿者们危险的消息,赶快撤离,他们无辜死亡,而我独活。怕悲剧真正的发生,而我会因为胆小懦弱而后半生受不了良心的煎熬!
那一个夜晚真难熬呀!生还是死?炙烤着我。
那是我们北京志愿者队伍快完成任务的最后一天下午,去小坝送救灾物资,路过桑枣镇。听说一个新疆来的红十字会志愿者团队愿意接收新的志愿者加入,我凭着可以给团队人员做心理辅导、做饭、后勤等手艺被这个队伍考虑可以留下来。因为在与死亡最亲密的接触中,志愿者要坚持下来,是最需要心里疏导的。队长让我签生死自愿书之前,最后叮嘱说:“如果男队员去各个村庄背粮食、送物资、抬尸体,给尸体打消毒针,忙不过来,女队员也要上,你行不行?”一瞬间,我的头皮子一下麻到脚跟。想象着我给尸体打针的样子,有点想吐,但还是克制住了。一阵莫名的英雄主义情结占了上风,让我咬着牙,肯定地说:“行,没有问题!”我把身份证号码、家里地址、父母联系电话等都写在了生死自愿书上,按上手印,签上名字,交给了队长。便于一旦出现意外,好与家人联系。我与队长约定好,在完成九州体育馆的救灾工作之后,就连夜返回桑枣镇的队伍。

在白溪河村的4队潇潇遇见了穆斯林的志愿者
我们从灾民聚集的九州体育馆,完成最后的任务离开时,已经晚上10点多了。为我们践行的几个绵阳的朋友,一直在等着我们吃晚饭。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北京来的志愿者团队将集体开车返回北京。当绵阳的朋友得知我吃完饭还要返回桑枣镇时,他们大吃一惊!说,在桑枣镇上方的堰塞湖随时都要垮塌,他们单位已接到通知,所有的工作人员、志愿者都已撤离,怎么还有人在那里?如果堰塞湖垮塌,两分钟之内,山洪就将淹没脚下的桑枣镇。大家有一些懵,估计是红十字会忘记通知这个新疆志愿者团队了。都纷纷劝我,不要回桑枣镇,想办法,明天通知到那个新疆团队赶快撤离就是。
去还是不去?生还是死?在我每一个细胞,每一滴血,每一根汗毛,每一寸皮肤,开始争吵,打架。我不想死!我知道,也许就在我去桑枣镇的路上,堰塞湖可能垮塌,或者在半夜某一个时刻,山洪凶猛冲下来,根本没有时间逃生。一个声音对我说:“潇潇,你一个女人,作为志愿者已经很棒了!回北京吧,不要去送死。太危险了!”另一个声音又说:“潇潇,如果你胆小,今晚没有去送信,明天新疆志愿者的30多条性命在洪水中丧生,你今后的日子都将在自责和后悔中度过!你真的不怕在这样的心魔中疯掉么?”这两个声音一直在撕扯着,我貌似平静地听着大家的好心劝告,其实心乱如麻。第三个声音占了上风:“潇潇,你平时内心蔑视那些软骨头,怎么事到临头也躲了?你做的是好事,老天会保佑的,你死不了,即使堰塞湖垮塌,你还是游泳高手呢!一定能侥幸逃生。”我在复杂的心绪中吃完了晚饭,这时接近夜晚12点了。我坚决深夜赶回桑枣镇的行为感动了大家,临行前,大家与我在送我去桑枣镇的车前拍了合影。千叮嘱,万叮呤要我注意安全。我清楚大家的沉重心情,也许这就是生离死别的最后一张留念。虽然,表面上都显得很轻松的样子,其实,我的内心深处也是这么想的。

在返回桑枣镇前一刻,潇潇与同车的志愿者张基忠和绵阳的朋友们合影
我到达桑枣镇已经是深夜2点左右了。志愿者们几乎在一整天的高强度劳动后,打着呼噜恢复疲劳。队长和另一位志愿者还没有睡下,握着手电在巡查。我压低激动的声音,把堰塞湖的险情告诉了队长。果然,他们不知情。我请队长马上与总部联系,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因为是深夜,红十字会只能第二天派车来撤离这批在桑枣镇被遗忘的最后的驻扎者。我们三人商量,先不要把险情告诉大家,怕乱了军心。等待天亮通知全体人员收拾东西撤离。队长和另一位志愿者帮助我把帐篷支起来,让我先睡觉。这一夜,我哪里敢睡着?五月中旬的桑枣镇,头上顶着随时要垮塌的堰塞湖,天气潮湿而闷热。我虽然精疲力尽,却更本没有睡意。我穿着外套躺下,汗水在衣服上洒下一圈又一圈盐。我把最重要的证件、细软都放进衣裤的口袋里扣好,以防山洪下来,随时逃生。这一夜,我迷迷糊糊听见死神在我的帐篷上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看见从堰塞湖缺口铺天盖地而下的洪水卷裹着粗大木桩,撞到我身边,我在挣扎,我在救人,我在逃生……这一夜,我在炼狱里来来回回……终于熬到了天亮,没有可怕的事发生。我们安全撤离了。
七
花语:在您的诗中,反复提及"死亡"一词,您对死亡的描述生动又贴切,如此深刻的人生感悟,从何而来?怯怯地问一句,您怕死吗?
潇潇:怕。这个怕是因为留给我的时间太短了,而我计划要完成的东西很多。比如运筹了很久的30余万字的长篇非虚构小说《性帝国》,以及已经写作了一部分的长诗《西藏唵嘛呢叭咪吽》,还有要主编的中国现代诗编年史丛书《前朦胧诗全集》《朦胧诗全集》《朦胧诗后全集》、执行主编《大诗歌》。这些不仅需要写作、思考、检索、查阅、归纳,还需要实地考察。比如去西藏的牧区体验生活。
对死亡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描述,往往与黑暗有关,与哭泣有关。但我不是这样的悲切。
我第一次离死亡最近,那是刚上小学的时候,我家保姆的妈妈去世了,我们去看她。那天阳光明媚,门廊亮堂,房间亮堂,她躺在木板上,盖着一张很白很白的单子。离我很近,我想看见她的脸,但看不见。我想那就是死亡的面孔。所以至今死亡在我心里没有那么晦涩,没有那么阴暗,它像一张白布单,或像白云一样缥缈。2004年10月,我坐黑鹰直升机去墨脱,翻越海拔5000米左右的多雄拉山口时,撞进了浓稠的云团,被撕扯,被纠缠。这时我看到死亡,看到了那朵飘渺的白云。

在西藏海拔接近5000米的错那潇潇与士兵在雪山上(摄于2004年)
八
花语:您主编过《前朦胧诗全集》、《朦胧诗全集》、《后朦胧诗全集》,那些被您编入诗集的作者,如今都是国内诗歌圈里的名家,不可否认您是一个好编辑,当初怎么想到编它们的?您对好诗的定义是什么?
潇潇:我对朦胧诗的关注是因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的存在给这个民族大多数人的心灵和灵魂留下了温暖的记忆。那时北岛、芒克、舒婷、顾城、梁小斌等朦胧诗群的诗歌,让我们长期受压抑、困惑的内心感到舒展,被意识禁锢的灵魂在诗人们的词语中开始飞翔。我记忆中,那个时期,几乎胸怀理想的人都会面向诗歌心潮澎湃,最漂亮的女性都围绕在诗人身边。
我对“前朦胧诗”的界定,可以这样简单来概括:即50年代未60年代初开始创作的诗人们的诗歌,就是北岛、芒克、舒婷、顾城他们之前的那一代人,更准确地说是被那段历史暂时遮蔽的一代文革时期的地下诗人的诗歌。而对“朦胧诗”的界定就省事得多,我是以北岛、芒克当年编的“今天诗群”为主,到“第三代”结束。“后朦胧诗”就以朦胧诗之后的“第三代诗群”为主了,用发展的眼光看,在我即将重编、修订的《朦胧诗后全集》中,我还将增补进70后、80后、90后优秀诗人的力作。
过去我们所知道的一些诗人,都是从教科书上学习来的主旋律的诗人,如郭小川、艾青、贺敬之、臧克家等。当“朦胧诗”兴起时,每当我读到北岛、芒克、顾城的作品就觉得奇怪,也很困惑,怎么感觉这些“朦胧诗”的源头并不是从艾青、臧克家、贺敬之他们那里流变而来的,无论从审美趣味上、语言方式上、精神气质上都不接轨,难道“朦胧诗”真是横空出世的?我坚信,在朦胧诗之前,一定有一段被遮蔽的精彩历史。后来看到杨建的一本书《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提到文革时期在北京有一些地下文学沙龙。他谈到地下沙龙中的一些诗人,说到郭世英,但是很简单,他收录的诗只有《小粪筐》一首,很像打油诗,也谈到了红卫兵时期的一些诗人,张郎郎、张寥寥、牟敦白、张新华等,不过都没有作品,但这群地下诗人的精神气息与写作形式却与“朦胧诗群”很接近。那时,我就萌生了如果有可能我一定要编一本与“朦胧诗”有最近血缘关系的诗歌选本,这就是后来我编《前朦胧诗全集》的初衷。

1995年秋,潇潇与诗友们的一次聚会(左起:邹静之、莫非、潇潇、严力、西川)
1993年我主编完《后朦胧诗全集》到北京,一次偶然的机会,与朋友聊天时才知道,原来这些当年活跃在北京地下文学沙龙的诗人们,大部分依然还在生活中苦苦地坚持着。后来通过牟敦白,一个“前朦胧诗”诗人,就认识了这个圈子里的一些老前辈,看到了他们当年写的诗歌手迹,这些诗当时从旧箱子里拿出来时纸张已经变黄,皱巴巴的。虽然当时他们大多数人在生活上很清苦,但是我发现这些诗人在精神上很可贵,我觉得比后代诗人更可贵的是,他们更理想主义、更具有一个诗人天生的浪漫情怀。在文学上、在心灵上,更有一种精神上的承担与使命感,他们与第三代以后的诗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后来我与"太阳纵队"的代表诗人张郎郎、张寥寥、牟敦白、鲁双芹、张新华、王东北在当时南池子张朗朗的家聚会了。我被他们在生活中流露出的纯真的诗意与浪漫情怀所感动,他们谈论诗歌时充满了神圣感,充满了虔诚。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聚会上,他们说今天的两代诗人们一定要走一走朱自清当年走过的小道,感受一下老人家笔下的荷塘月色。当时在他们眼里,我还是一个小姑娘,但知道我正在雄心勃勃打算编纂“中国现代诗编年史丛书” 《前朦胧诗全集》、《朦胧诗全集》、《后朦胧诗全集》、《中国先锋诗歌批评全集》,知道我对诗歌的热爱与执著,自然而然就把我算下一代诗人了,虽然,我们中间还隔着一代“朦胧诗”诗人。记得旁晚时分,是张新华从家里抱来吉他,一边弹,大家就一边唱俄罗斯民歌,后来在朱自清写过的荷塘月色中,大家又纷纷开始朗诵诗歌,特别是他们对唐诗宋词的博闻强记以及古典文化的修养,让我暗自佩服。在1993年的夏天,我几乎见到了“前朦胧诗”时代的所有在北京的诗人。他们还有依群、食指、黄翔等。再后来,我见到了郭世英的妹妹郭平英,在郭沫若的纪念馆,是她与周国平商量,把郭沫若当年为纪念儿子郭世英之死而抄写在家书上的郭世英的诗歌整理好了,由周国平亲笔抄写给我的。我的心沉甸甸的,从我收集到的大量诗稿中,我兴奋地发现,这正是我寻找的产生“朦胧诗”最初的土壤与气候。可以说,中国现代诗的发端,正是从这些在六十年代初就曾活跃于一些不公开的艺术小团体,秘密文艺沙龙中的一代青年诗人开始的,然后到“朦胧诗”时期在北岛、芒克、舒婷、顾城、等诗人那里开花、结果。从60年代初郭世英的诗歌中就足以看到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由于像郭世英这样的一批年青诗人,以生命的坠落而开端的!
在诗歌逐步走向小众,走向偏狭的当下诗坛的乱象中,我认为的好诗是那些能够坚持探索,以诗歌的良知回应现实,胸怀时代与未来精神的、具有探索性意义的诗歌文本,为我们的时代与历史检验与凸现当下生存与精神的多元而丰富的生命意义与价值朝向。这种追求,在于我们力图为我们的读者呈现具有探索精神与艺术个性鲜明、风格异彩纷呈的当代诗歌。简单来说,第一应该有批评指向,第二语言要灵动、创新,意象要广博、丰富。第三要走心,有温度。
九
花语:您画的油画,每一幅都很有趣,每一幅都配了自己的诗在上面,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
潇潇:是的。色彩不能代表全部。诗配画的目的,是因为画不能完全表达我的心境,而诗可以为我的画进行无边的延续。有时是一首诗先诞生,有时是一幅画面先出现。而画实际上是对我诗句的一种凝练,而这种凝练我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把它模糊。我认为好的画家也是诗人。绘画是诗意的色彩构图,诗歌是色彩绘画的想象,是语言的绘画。

潇潇与阿多尼斯在青海湖国际诗歌节。
十
花语:在诗歌和绘画之外,您是个什么样的人,能否概括一下?
潇潇:是一个懒人,不太会安排时间。每天会琢磨做点好吃的慰劳自己。总是想拒绝一些酒会、聚会、饭局,但没有能力拒绝。兴致高的时候干活就会干上两天两夜,像泥瓦匠,挺辛苦的。散淡的时候多一些,时光怎么流走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就这样吧,已经习惯了。只是想起死神的时候,有点让人烦!
十一
花语:看您的简介,我发现作为中国最优秀的诗人之一,您既没有加入任何地方作协,更没有加入中国作协。但是,颇有意味的是,在很多大型的活动上,您是当然的主持人。您就像一个无门无派的高手,没有拿何任利器,却处处高人一筹,近年,更是拿奖拿到手软,“无冕之王”一词很适合您,能否说说,您为什么没有加入任何作协,也没加入什么圈子或帮派?
潇潇:前面说过,我骨子里是个慵懒的人。喜欢自由自在,笑傲江湖,不被管束。如果参加某个圈子或帮派、作协,我就要对人家负责任,尽义务。这就像婚姻,你嫁给了人家,你就不能乱来,你就要承担责任,尽本份。哈哈!

第三届德令哈海子青年诗歌节主持人潇潇,图为潇潇请海子母亲朗诵诗歌
这些年,一不小心我就被主持了,都是酷爱诗歌,友情帮忙。的确,我主持了无数中外诗歌节、国际诗歌周的高峰论坛和诗人的诗歌朗诵,以及诗歌春晚、诗歌颁奖典礼等。几乎每次到现场,才知道主办方的具体安排和内容,他们太高估我的能力了,我不得不临阵磨枪,常常脱口秀。也有被大风和寒冷吹翻在台上的时候,比如这届德令哈海子青年诗歌节的摇滚朗诵之夜,那时,我要有武功秘籍就好了!让一夜大风和寒冷统统还给温暖!
来源:中国诗歌网
供稿:北京城市未来文化艺术中心